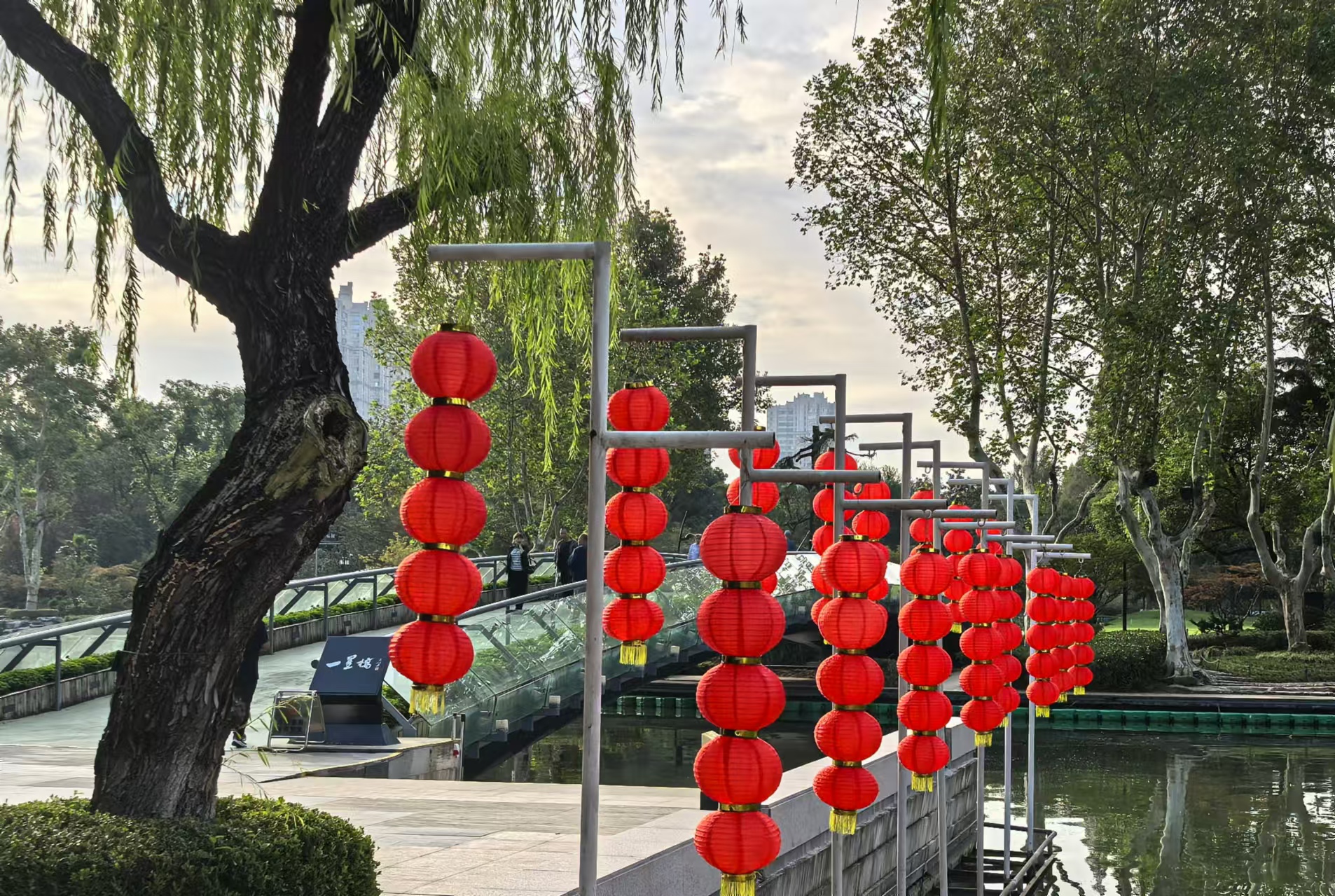除去近年引入的社会科学实证研究方法外,在主流的研究范式上,法学或者法律研究在涉及行为和决策研究时,长期以来不重视精确性和数学演绎。作为一门社会科学,其倾向于将决策过程的人脑“黑箱”基本上归结为偏哲学意义上的“自由意志”,漠视决策的内在过程及机理,仅以外在行为表现推测主观状态/意图,再决定其责任、后果。
关于心智、决策的背景虽然不是主流法学重点关注的内容,但法学研究依然需要基于人性及心智。法教义学对于人性的假设,也是基于19世纪心理学和人性论的基本理论和假设。然而,经历了一两百年的社会进步,人性虽然不变,但对于人性、心智和决策的研究已经由人性论式的假设,推进为心理学、人类学的实证研究,再推进到神经科学、基因、演化(博弈)论的精确研究。这三个精确的学科,分别代表着决策/行为的当下决策、历史背景以及理性知识分析这三个维度。
而随着大数据、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,相关技术和思维模式已经能够部分运用于司法、治理的实践。大数据的精确性,体现为外在的社会群体性。而决策的内在精确性——认知神经科学的重要性,也需要主流法学界、法律界予以关注。在神经(元)政治学、神经(元)伦理学乃至实验哲学已经在域外学术界蓬勃发展的今日,在西方国家已经开展了大量的行为法学研究并开始进行神经(元)法学研究的背景下,在国内进行相关学术研究就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。
在这种背景下,《心智、大脑与法律:法律神经科学的概念基础》一书译介进入国内具有重要意义。该书对于法律神经科学或神经法学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法律基本原理、事实认定和刑事法律这三个领域:
第一个部分讨论法律基本问题,其以认知神经科学的范式研究各类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性问题,具有较强的学科交叉意义,也体现了法学理论与神经科学、心智理论的基础性关系;法学可以借鉴相关神经社会科学的实验和理论,并可以尝试模仿相关的研究范式。这方面的内容能够从新的思考视角、范式对人性、德行的基本问题进行研究。
第二个部分是事实认定问题,主要是关于测谎的问题。相比现有的测谎技术可能导致一些失真,EEG(脑电图)技术能够深入到记忆的神经工作机制中进行测量,在若干的识别模式中(例如是否见过某物)基本上确保近100%的正确率。该书在此领域的研究还涉及证据的科学性问题,而证据科学界相较于传统的法教义学界而言更能够接受此类研究。
第三个部分主要从神经科学的视角研究犯罪与刑罚问题,特别是研究犯罪行为、意图以及精神问题。这方面其实是犯罪学问题,而在犯罪学学界类似研究已有较长的传统,等等。
而该书所指的大脑,是适应普遍通行的关于脑部神经系统的说法,是指脑部或者人脑。从功能角度看,人的脑部神经至少可以分成三个部分:第一个部分负责动物性的基本功能。第二个是情感脑系统,专司人类之间的社会交往。第三个以额叶等脑皮层为主,负责理性思维以及综合决策。与法学相关的主要是情感脑区和理性脑区。在经济学、伦理学等与神经科学之间的交叉研究中,已经发现了诸多功能性脑区与决策行为之间的对应关系。由此,相关专业领域内的行为与决策的“黑箱”正在被神经实验研究逐渐揭示为“灰箱”甚至“白箱”,这也有利于今后法学与心智、神经科学的交叉研究。
除了该书上述内容外,法学与心智、神经科学的交叉研究还有很多领域值得研究。例如一个重要的领域是民商法、经济法的神经基础研究;近些年在神经元经济学已经有若干涉及契约、合作方面的研究。例如在契约合作中关于“声誉”/“信任”的神经学研究;此外,还有关于社会性契约规则的神经研究等。在这些领域,神经元经济学已经进行了相当的研究,若干研究也能够与民商法、经济法进行结合,其实也有比较大的研究基础和空间。
此外,在当下研究心智问题,还涉及机器的心智——人工智能。早年人工智能学界有部分学者长期关注人脑的神经科学研究,在当下的人工智能热度高涨之后,又有国内外学者发起了各类“脑科学与人工智能”的研究计划。而不断发展的技术又涉及脑机接口、人脑仿生研究等,其又可能给相关研究提供新的机会和问题。此外,当下另一个热点的大数据研究就本质而言其实是行为学研究,这与神经学研究仅仅是一纸之隔。法律与神经科学的交叉研究也一定能够具有前景,虽然其可能仅仅在小众的、高端的领域,而不一定会成为社会性热点。
而从个体的内在决策方面,当下存在对于心智的不同意见。在多数程度上看,“具身心智”理论与“自由意志”的预设存在较为强烈的冲突。一类是最近二三十年来,西方的认知心理学界、心智学说领域兴起的“具身心智”理论,强调决策、意识的生理(神经)基础。依此理论,自由意志受到强烈的生理限制。最近一二十年认知神经学界以此为基本出发点进行大量的生理、神经实验(标志性的如有实验能够从某个角度部分证明自由意志是受到限制的)。另一类意见则是对传统“自由意志”的坚持,正如强调道德理性的康德认为“偏好和反感”都是一种“任性的病理学”,而自由意志是可以超越这些“任性的病理学”。而有磁共振实验能够证明主意识对于思维及其神经成像结果的控制,这也许是人类心智的极为高明之处。当然了,双方还没有很直接的系列实验以完全确证自己的观点;相关的实验和争论依然在热烈进行之中。
难度大意味着各类机遇就会较大,因为所有的重大突破,均是在人类知识的边缘地带产生突破的。法学研究者,或许也应加入或者围观相关的学术探险之旅。
(作者为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)